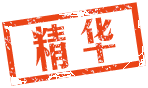本帖最后由 老骨头儿 于 2019-9-25 10:16 编辑
微信群里,大家虽天南海北人情世故话题万千,聊者侃侃而谈高谈阔论,听者有滋有味饶有兴趣。虽每每想凑上一两句,却乃才疏学浅腹中空空,总觉得无法接上话茬。虽如此,却也发现,群友们念念不忘的还是野鹤先生家里种着的那几根甘蔗。从播种到出苗,从长高到长粗,从培土到灌水,从抓贼到尝鲜,从遥远到临近,一直是大家涉及最多的地方吧。 记忆里已经上小学的我,受不了同学们的诱惑,在一个周六的午后与几个玩伴随着大人到五六里远的麻车村看榨糖。这也应该是自己离开父母与姐姐眼光第一次出远门吧。 那时没有什么大路,有的尽是此小泥路,本就很窄的路面上,还时不时被挖上几个大小的流水用的田缺口,然后随随便便放上块石头方便行车走路。路两旁的庄稼叶与杂草,时不时横向路中,挑逗性扯你几下。最让人担心的是,路两旁都是糖梗地的小路,种着的糖粳叶将小路遮得阴森森的,糖梗叶也会在你不经意时将你的小手臂拉出几道口子。在这样的小路上行走得特别的小心,既怕稍不留神摔上一跤,又怕冷不防从庄稼地里跑出只狼来。随着大人行走一段时间后已经开始后悔,走那么远,怕找不到回家的路,可更怕独自回走。就在这样的忐忑里,经过漫长煎熬,终于闻到了远处随风飘来的阵阵糖香,也慢慢听到了嘈杂的喧哗声,麻车村到了。 糖车就在一块空旷的庄稼地中央,两头牛被蒙住了眼慢慢的转圈,牛身上绑着一根粗长的弓木,带动着中间比大人还高的两个木圆柱相向转动,大木柱紧紧绞合在一起,将一根根糖粳碾得粉碎,挤出浊黑色的糖汁水,缓缓流向边上深埋的大缸里,然后再一担担挑到最靠近灶口的灶锅里制红糖。那样的大锅台也是从没见过,连着十多口从大到小的铁锅,还有那个高耸的烟囱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榨糖的情形。 糖很香,用途大,人人喜欢,但榨糖、熬糖却有相当大的危险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完全靠牛力榨糖的时候。村里有一个人在糖车里喂糖粳时因为不小心,一只手被夹入到了两个大圆柱间,幸亏赶牛的及时听到惨叫及时拉停牛将糖车停住。那人虽保住生命,却失去了一条前臂。还有,大人常常告诫我们,绝对不能靠近热气腾腾满是透人香味的糖锅。糖水炼制红糖,需要将糖水从大锅一口口往小锅里舀,一边边的炼,难免会洒出一些带着点粘性的糖水,人站在锅边,非常容易出危险,经常听到什么榨糖厂有人滑入糖锅的事。 七十年代末,公社在村边的一个小村里办起了一个榨糖厂。那时的糖车已经升级成榨糖机,不仅速度加快了许多,也更安全了。虽然如今糖作为地域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得到扶持发展,糖厂到处林立,但那时榨糖的确比如今的香多啦。上学的地方与糖厂相距三里多,总能时不时飘过几阵糖香。特别是临近中午时,肚子咕咕作响,糖香惹得我们口水直流心神不定,只能狠狠吮吸带糖味的空气罢了。而糖厂办在自己村边,最开心的事就是在放学时,眼看着一车车糖粳拉过去,看着大人跟在车后冷不防抽一两根逃走的情形,想着自己鼓起勇气也试上一把,却也从不敢去尝试。 常态下的红糖非常蓬散。制糖时技术稍不过关,就会出现一种叫作是“斧头派”的红糖。集体时大家最喜欢这种红糖,因为好的红糖要卖给国家,最多也只能分个一两斤留下过年过节用。斧头派顾名思义就是红糖结得像石头一样硬,需要用斧头砍柴一样才能劈开劈散。其实斧头派并不是红糖的次品,只是品相上不好看,国家也不收购,但并不会影响食用。所以如果生产队里榨糖时出现了斧头派,虽然有损失,但全队上下都会很开心,因为这些斧头派可以全部分给各户。分到各家的斧头派不易长期保存,也就舍得给小孩吃了。这时是小孩们最开心的时候,人人手拿一小块斧头派,像棒冰似的放嘴里吮吸,虽化不了多少,但嘴角上被红色涂满了,硬红糖粘着牙齿,甜得不能再甜。特别是红糖水与口水混在一起往下淌,只得伸长舌头在嘴边舔,然后再继续吮吸再继续舔。 那滋那味,以及朦胧的幸福感,都交融在这浓浓的甘甜的回忆里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