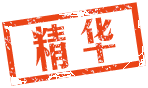该用户从未签到
金牌会员
 
- 积分
- 11618
- 金钱
- 4128
- 威望
- 1394
- 精华
- 7
- 注册时间
- 2011-5-19
|
本帖最后由 淡墨斋 于 2019-10-6 17:57 编辑
湮没的俞宅
怪石嶙峋/文
北宋宣和年间,浙中婺州府义乌县南门外约十里,地名永青岩俞宅,有一世家,姓俞,名光明,表字东亮,婚配安人王氏,相继产下一男一女,起名俞金、俞玉。俞家田产广延,家财万贯,三个哥哥又在京城为官,因此上,便仗着势力,欺邻吓舍,作威作福,连本县太尹也让他三分。
俞宅东墙外,有田地五石,乃是陈远志所有。这陈远志,安徽徽州府歙县人氏,在义乌县朱店街开一间茶叶铺儿,专做祁门红茶、太平猴魁、黄山茅峰、六安瓜片、屯溪绿茶、霍山黄芽、岳西翠兰、泾县特尖、涌溪火青、桐城小花……的买卖,生意颇颇得过。邻铺骆裁缝,见陈远志为人厚道本分,手头又活,料想女儿嫁他不至受苦,便把女儿许了他,做成了一门亲事。
俞东亮家大业大,四邻八乡俱有田产,每逢秋割,粮仓则不够用度。有心想在东墙外靠出一个粮仓,却又是陈远志的田地,心下懊恼不已。管家荣保皮不以为然,献计道:“员外何不另择良田,与那陈远志置换?倘然不肯通融,拼出去多给一股银子,看他如何不上火?怕是双手奉上哩!”俞东亮道:“好虽好,只是尊卑有别,我去仰其鼻息央人,传出去被人笑话。”荣保皮道:“员外放心,区区小事,包在小人身上。”俞东亮闻言,心中大喜。
次日清早,荣保皮穿戴整齐,拎了一副茶枣糕,走进陈记茶叶铺里。陈远志拱手问道:“今日大管家如何得暇,来小店里坐坐?”荣保皮笑颜上颊,说道:“非为别事!特来与陈掌柜置换一样东西。”陈远志笑道:“大管家吃着东家的、住着东家的、花着东家的,缺甚东西,倒与寒家置换?”荣保皮说道:“俞宅东墙外,是你家田地。我家员外另择良田,意欲与你一比一置换,用来建造粮仓,不知陈掌柜尊意如何?”陈远志说道:“这五石薄田,是小可千辛万苦挣下来的家业,如何舍得置换?”荣保皮脸色一沉,问道:“再添你一成红利,意下如何?”陈远志断然道:“田畴上有一所香火殿,塑着一尊五谷神,若是置换与员外建造粮仓,岂不拆了殿阁?冒犯神灵时,不是耍处!大管家不必多言。不换!不换!”荣保皮肿起一个猪肝脸,拂袖而出。行不多远,又蹬蹬蹬折了回来,拎起茶枣糕出门去了。
这荣保皮在茶叶铺里碰了一鼻子灰,心中老大的不悦,想道:“我前日口无遮拦,在员外跟前打下包票,今日无功而返,必被员外看轻。怎生是好?”一头走,一头想着如何应付。回到宅上,便添花添草,把个陈远志说得一无是处。俞东亮骂道:“你这蠢才,怎不说是我的意思?”荣保皮装起一脸委屈,说道:“员外有所不知,不提你还好哩!提起员外时,他越发无礼了。”俞东亮脸一沉,厉声问道:“怎么说?”荣保皮撒个谎:“陈远志大骂,员外倚靠哥哥,分明是狗仗人势,别人怕你,陈远志却是不怕。”俞东亮心中大怒,脸上青一阵,红一阵,便起了不良之意。正是:寒天喝冷水,点点在心头。
忽一日,俞东亮应孙押师相邀,乘了一顶轿子,赴徐陋巷酒肆里小聚。衙门李捕头、张孔目、黄班头等俱已到齐。众人一一见过礼,分宾主坐定。俞东亮说道:“押师设筵,何当厚扰?今日俞某做东,少时向列位尊兄讨教清诲,万望不拒。”孙押师笑着说道:“兄弟之间,何分彼此?我等逐日为客,今日做一回主,聊表寸心。”说罢,吩咐酒保列上酒肴,众人吆五喝六划起拳来。
也是陈远志命里该有一劫。这个时候,却见巡捕毛进,推开隔间门,来雅座里与李捕头说话。毛进喜上眉梢,说道:“捕头哥哥!好事来了!”李捕头丈二的和尚摸不著头脑,问道:“甚么好事?”毛进说道:“昨夜在平昌顺擒住了独脚大盗,人赃俱获哩!正囚在牢里候审。”原来,半月之内,城中多有大户被盗,纷纷告状。太尹责成李捕头限时缉捕盗贼。李捕头这几日正在愁闷,不想盗贼自撞进罗网,却不造化?
俞东亮心生一计,对众人说道:“列位尊兄!俞某欲借贼人一用。”众人惊愕不已,问道:“量一个贼骨头,有甚用处?”俞东亮恨恨说道:“前番与陈远志置换田地,泼才不肯通融犹有则可,反被他羞辱了一顿。若能消得这口恶气,绝不亏待列位尊兄。”孙押师说道:“大员外吩咐,我等敢不从命?此事只在张孔目身上。”
吃罢酒,众人一齐回衙。张孔目说道:“今日借刀杀人,不可直来直去,须转弯抹角,迂回吃住他。”李捕头是个粗货,搓着手问道:“那怎么办?”张孔目说道:“贼骨头乃是山里核桃,需敲敲吃。把他往死里打,他便两害相较取其轻哩!”说罢,使了一个眼色。李捕头会意,着四五个巡捕,手执水火棍,你一棍,我一棍,直打得贼骨头一佛升天,二佛出世。张孔目看看火候到了,屏退众人,对贼人悄悄说道:“明日过堂,你只需如此这般,自有人捞你出了苦海,若道半个不字,教你粉身碎骨。”贼人哭丧着脸,求饶道:“小人的性命,攥在爷爷手里,明日遵命便了。”
次日,太尹升堂。黄班头自囚牢里提出人犯,命他跪于案前。太尹问:“下跪何人?家住哪府哪县?”贼人答:“苦人儿莫彦克,岭南桂林府人氏。”太尹问:“因何爬墙越壁,入室盗窃?从实招供,免受皮肉之苦。”莫彦克答:“小人流落义乌,盘缠用尽,口食不周,蒙朱店街茶叶铺陈远志指点,在城中富家发些利市。”太尹问:“赃物、赃款现在何处?”莫彦克答:“素由陈掌柜保管,与他三七分账。”刑房张孔目做了笔录。太尹命皂隶牵莫彦克下堂,传令拘拿陈远志。
少时,陈远志被拘于堂上。太尹问:“下跪的可是陈远志?”陈远志答:“正是草民。”太尹问:“你私通贼人,坐地分账,细细招来!”陈远志答:“草民本本分分做着茶叶经纪,怎会私通贼寇,坐地分账?”太尹问:“认得莫彦克么?”陈远志答:“不认得。”太尹思忖,陈远志生得斯文,恁样一个生意人,如何为盗?本案还须细细推勘。当即唤过衙役,在耳畔嘀咕了几句。衙役自转入后堂去了。
不一会,三人并跪于陈远志左右。太尹道:“传莫彦克!”黄班头不敢怠慢,牵着莫彦克二次上堂。太尹道:“ 莫彦克!你去指认陈远志,二人当堂对质。”这贼胚,哪里认得陈远志?正要胡乱指认。黄班头见状,背朝太尹,对着陈远志撇嘴。莫彦克一点即透,指着陈远志道:“大哥!休怪做兄弟的嘴巴不牢,我也是熬刑不过哩!事以至此,还是从实招了吧!”陈远志一股无名孽火自胸中窜起,大骂道:“放你娘的臭狗屁!天杀的泼贼!谁是你大哥?哪个与你坐地分账?在这里血口喷人,今日少不得与你拼命。”一头撞去,扭住莫彦克便打。太尹勃然大怒:“市井狂徒,咆哮公堂,不动大刑,量你不招。来呀!将陈远志拉下去重责四十大板。”皂隶如狼似虎,架出陈远志按在刑凳上,直打得他皮开肉绽。正是:囚笼子可畏,水火棍堪哀,拶子刑最惨,木夹棍伤哉,老虎凳上不招来,换个白鹤亮翅飞。
可怜陈远志,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,被贼人咬住不放,哪里能洗得清白?刑毕,皂隶依旧架回陈远志。太尹问:“招也不招?”陈远志答:“草民愿招。”当下,太尹三推六问,陈远志一一作答,张孔目做了笔录,孙押师做了档案。太尹命二犯当堂画押,吩咐上了枷锁,禁二人于狱中。
贼人莫彦克收在监中,日日巴望着张孔目来捞救出狱,却是哪里能够如愿的?而狱中又热又湿,自己又没钱用度,吃的又比猪狗还差上三分,加上棍伤发作,得了寒湿燥热症,不久便病死在狱中。
且说骆氏,自丈夫蒙冤以来,日夜啼哭。骆公心疼女儿,三天两头走跳在义乌县衙门里,替女婿上下疏通,因此上,陈远志在狱中倒也没有受苦。
一日,骆公又往衙门里去探口风,正好遇着俞东亮。俞东亮佯装不知,问道:“丈丈来衙门里,有甚公干?”骆公像吃了一剂苦药,哭丧着脸说道:“老汉一个女婿,也不知什么事犯了祖坟,平白无故被一个贼人诬陷,蒙受不白之冤,如今还囚在牢里,不知如何是好。”俞东亮睁大双眼,惊讶道:“有这等事?丈丈怎不早说,俞某或能尽一份绵薄之力。”骆公活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激动不已,说道:“大员外佛眼相看,小婿便有救了。老汉给恩人磕头!”骆公拜倒在地,磕了三个响头,禁不住老泪纵横。俞东亮说道:“我们乡里乡亲,肉面对着肉孔,丈丈何需客套?不过,若要搭救令婿出得苦海,上下关节疏通,追赃纳库这两项,少说也得纹银千两。”骆公愁道:“寻常人家,哪有这许多银两?容老汉回家与女儿商议,明日一定回复大员外。”俞东亮说道:“事不宜迟,丈丈要早作打算。”这骆公,将仇作恩,把俞东亮当作救命活菩萨,千托万托了一番。
得了俞东亮的许诺,骆公的心情也好了起来,走起路来十个脚丫子朝天,恨不得十尺路缩作一尺走,急匆匆回家与女儿报信。方才进了家门,便对女儿说道:“今日爹爹去衙门里探口风,遇着一个贵人了。”骆氏问道:“贵人阿谁?”骆公说道:“便是田邻居俞员外,答应爹爹搭救远志,好人哩!”骆氏转悲为喜,说道:“待我谢天谢地!”骆公叹息起来:“只是纹银千两,告借无门。为今之计,有二条路选择。”骆氏疑惑,问道:“哪两条路?”骆公说道:“一条,盘掉茶叶铺、卖掉田产,筹措银两救人;二条,他自命薄,须怨不得你,逼他写得一纸休书,将你另配他人,莫教蹉跎了青春。”骆氏又哭将起来,说道:“我与陈郎,一日夫妻,百日恩情,陈郎有个三长两短,女儿有死而已!岂能一家女儿吃两家菜?爹爹若能搭救陈郎,便是倾家荡产,也在所不惜!”骆公见女儿意坚志决,出门寻找中人去了。
次日清早,骆公匆匆扒下早饭,便来俞宅回复。俞东亮说道:“与丈丈报一个好消息,一个坏消息。”骆公问道:“怎么说?”俞东亮说道:“太尹看俞某三分薄面,答应保释令婿,此好消息;正犯已病死在狱中,令婿即便蒙冤莫白,也是死无对证,况令婿有供词画押,这赃款退赔是免不得了,此坏消息。”骆公得了喜讯,千恩万谢地出了俞宅。
三日后,骆公“口干吃盐卤”,央中人寻着受主,将茶叶铺儿、五石田产作价七百两,半卖半送出脱掉了。为补足三百两缺口,骆氏典当掉了首饰,骆公卖掉了房屋,连防老的棺材本也搭进去了。凑足一千两纹银,陈、龚两家财产,便如同清水荡洗过一般,干干净净。
陈远志出狱后,上无片瓦遮身,下无立锥之地,又羞见故人,便带上岳父与浑家,在义乌县盐埠头下船,经东阳江、婺江、兰江、新安江,回安徽歙县老家安身。
俞东亮得了一千两雪花银,替陈远志退赃了二百两、衙门上下打点了三百两、余下五百两正是自家买下陈家田产的份额,这银子转了一个弯,又回到了自己手里,还白得了五石田产。
不久,俞东亮请了风水先生,罗盘定了粮仓朝向。拆殿阁,毁神像,在新购置的田地上破土动工,修建了四排粮仓。
五谷神大恼,便走到城隍庙里去诉苦。义乌县城隍显佑伯,查勘罢《生死簿》、《功过录》,说道:“世人作恶,每以自解,而不知昭昭之祸,即冥冥之罚。俞东亮阳寿六十七岁,遵阴司刑律,诬良为盗罚寿十岁、强占民田罚寿十岁、拆毁佛地罚寿十岁,今年三十七岁,宜付诸天道报施。”五谷神得了准信儿,作别城隍,自往别处入神位去了。
一夜,俞东亮才就枕,王氏对他说道:“员外!我家富甲一方,一不愁吃的,二不愁穿的,却恁样做家,从不曾撒漫使钱。如今有伯伯们在东京做靠山,何不带俞金、俞玉去天子皇城长长见识?又能耗费得几何?”俞东亮说道:“家事恁样忙,如何脱得开身?”王氏答道:“荣管家能写会算,为人又勤谨,家事把与他打理,料想并无闪失。我们出门十天半月,即刻回程便了。”俞东亮笑道:“妇道人家好不晓事,此去东京,山长水远,音问阻隔。你道去外婆家么,十天半月能够回程?”王氏说道:“千里之遥,权当沿途观赏景致,却不更好?伯伯们在东京做官,依样从家里出门哩!何况同胞骨肉,多年未有团聚,人生在世,不就图个快活受用么?”俞东亮的耳朵是棉花做的,被老婆念了一通“床头经”,便依了她的言语,决定携家眷去东京城里走一遭,与哥哥们团聚。
靖康元年孟秋,俞东亮检点了家中库存,备足盘缠,雇了一只大船,连同丫头、养娘、伙计,一家七口在佛堂浮桥码头下船,往东京省亲。当日,孙押师、李捕头、张孔目、黄班头、荣保皮,都来码头送行。俞东亮对荣保皮说道:“此去东京,少则三月,多则半年,荣管家须好生看管家园,待我回来,自有重赏。”荣保皮道:“员外但请放心,小人在帐目上,一出一入,毫厘不爽。”俞东亮与众人作别,吩咐梢公起锚。大船鼓起满风帆,沿东阳江、婺江、兰江、富春江、钱塘江、京杭大运河、黄河航行,不止一日,便在东京停泊。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这俞东亮进了东京城,一似飞蛾扑灯一般,有脚去,无脚回。却是为何?原来,金兀术率金兵渡过黄河,把东京城围得水泄不通。靖康元年十二月,东京城被攻破。金兵入城,奸淫掳掠,杀人如麻,俞氏阖家皆遭兵燹之灾,一家十八口尽被金兵杀戮。正是:是是非非天,杳杳冥冥地;狠计总徒然,害人终害己。
且说荣保皮,自东家出门以来,宅上一应事务,都经他过手,俨然成了新主人,逐日做起大来。丫头使女,田头伙计,一家三十余口人,尽由他使唤,稍有不顺,轻则训骂,重则挨打。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,只得小心伺候着。
俞家有一个使女,唤做茉莉,生得肌肤似雪,明眸皓齿,姿态甚美,乃是俞东亮的姘头,只因王氏不能相容,故一直未公开。一日,天色向晚,茉莉来寻荣管家支月钱。荣保皮心下十分欢喜,平时早就注目着,只是员外在家,碍上碍下,不敢造次。如今自己做大了,未免胆大,软眯眯地酥着眼睛,问道:“茉莉妹妹!来俞家几年了?”茉莉答道:“自十二岁进得俞家,至今已八年整了。”荣保皮撩拨道:“青春二十,正值妙龄,如何耐得住寂寞?”茉莉说道:“奴奴生得粗蠢,好人家一向不屑于联姻,只得在俞家终老。”荣保皮挤眉弄眼,说道:“有心与茉莉妹妹寻媒说合,不知中意恁样人家?”茉莉看出荣保皮在下钩,心下也自乐意,柔声细语道:“便要嫁人,也须是大管家这等人才,方才称心如意。”荣保皮见时机成熟,立起身来,一把抱住茉莉,狗啃食一般做了一个“吕”字。二人你贪我爱,滚做一堆。当晚,茉莉留宿在荣保皮房中,做了露水夫妻。
过了月余,茉莉道:“我夜夜出入你的房中,难免被人起疑。若是员外回来了,有人暗中颠唇簸嘴,怎生是好?”这荣保皮做惯了奴才,一向对主子恭恭敬敬,今番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充大王”,不免小人得志,托起大来,说道:“拼着与员外反目成仇,也要吞他一股家私,将来与娘子做了长头夫妻,正好受用。”茉莉道:“奴家跟着员外,无名无份,永无个出头的日子,有甚么盼头?跟着荣郎,还指望日后相夫教子,举案齐眉。正所谓‘量小非君子,无毒不丈夫’,荣郎宜早早盘算。”
常言道:“妻贤夫祸少,子孝父心宽。”这荣保皮,自那日听了妇人的言语,便瞒着帐房先生,在钱粮一出一入之间动起了手脚,不出半年,即私藏了千两纹银。帐房先生看在眼里,只是不敢揭穿,索性等东家回来,再作区处。谁知左盼右等,并不见俞东亮回程。
会值七月半,帐房先生借故回家烧香,折进了衙门里,与孙押师将荣管家如何私通茉莉、侵吞钱粮,一五一十说与备细。孙押师骂道:“背主刁奴,岂肯饶他?”当即与张孔目商议。张孔目说道:“这事一些也不难!”孙押师问道:“孔目如此轻描淡写,却是为何?”张孔目说道:“烦劳押师写两封家书,一封寄至东京俞府,催促员外赶紧回程;一封寄至俞宅敲山震虎,刁奴必然收敛一段时日。等员外回来,再收拾刁奴,也为时不晚。”孙押师赞道:“此计甚妙!”当下,孙押师拟好家书,寻出一个老信封,小心剔下封皮,贴在冒牌信封上,吩咐邮差投递到俞宅。
荣保皮收到家书,慌得六神无主,对茉莉道:“员外在东京玩得转,靠着三个哥哥,在吏部里捐了一个县丞,不日将回义乌上任。这私吞银两,尚可填补,与你私通,未必饶得过我。娘子!你我缘分尽矣!”说罢,扑簌簌地掉下两行眼泪来。茉莉骂道:“老大一个汉子,事到其中却做缩头乌龟,羞也不羞?你把我抛撇开了,他回来做了县丞,肯饶过你,饶过我?”茉莉一席话,惊醒了梦中人。荣保皮将心一横,做出一场罪恶来。正是:眼孔浅时无量大,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当夜更深人静,荣保皮把纹银分装进两个酒坛子里,坛口封上麦芒泥,领口插一碗灯笼,挑着去南山里埋藏。
南山从东至西,山势绵延起伏数十里,由南往北,叫作八岭坑,乃是一条十里长的山垄。山中林丰草茂,岭上峰岩重叠,构筑起一幅巨大的天然屏障,把义乌与南东阳一分为二。
荣保皮行至山嘴,心中想道:“一不做,二不休;人不谋,家不富。我把俞宅一把火烧了,下人们无处容身,便树倒猢狲散了。员外回来时,只道各自散伙,官府也不便追究哩!直待风头过去,挖出银子与茉莉远走高飞,却不快活受用?”想到这里,便把钱担子藏在一个隐蔽处,吹灭灯笼,摸黑折回宅上。踮起脚尖爬上柴楼,点燃了四个火头,乘着夜色掩护,逃离了现场。
荣保皮深一脚,浅一脚,沿着山垄翻过分水岭,在一座峰岩下停了下来。这一处峰岩,嶙嶙峋峋,乱石纵横,内有一个洞穴,洞口被一堵荆棘墙覆盖着,莫说是寻常人,便是樵夫也自不知。荣保皮四顾无人,撩开荆棘钻入洞中。石洞不甚大,约有一丈见方,虽说四周都是岩石,脚下却是泥沙。他在角落里挖掇出一个深坑,将两只坛子埋了进去,填平泥沙,竟看不出破绽来。
这刁奴才,折腾了大半夜,累得像一条狗,瘫在地上,不住地喘着粗气,自言自语道:“且在洞里坐等天明,明早下山寻着茉莉,带出去躲避一阵,等风声一过,便万事大吉了。”岂料,人有千算,不及老天一算。荣保皮正在得意之间,忽闻沙沙作响,一股腥味扑鼻而来。只见一条蝮蛇人立而起,噗噗喷出毒气。荣保皮一阵心惊肉跳,起身夺路而奔。蛇暴进如风,一口啄中他的面门,蜿蜒着出洞而去。荣保皮血流满面,未及抹去,便双眼模糊,神志不清,一跤扑倒,直挺挺地死在了洞中。正是:地狱受苦何人见,万般自作还自受。
却说俞宅,那大火烧将起来,烈焰张天,火光夺月。高空上恰似数驾乌龙翻滚,屋宇内宛如万条金蛇吐信。丫头使女们披头散发,纷纷逃出屋外呼叫;家丁伙计们惟恐领不着月钱,一齐冲进银库里“抢火局”。一时间,铜锣敲击声、呼男唤女声、妇啼儿哭声、火爆哔卜声、抢钱打斗声、瓦片散落琅琅声、墙体坍塌轰然声……百千齐作,闹哄哄地乱作一团。
比及四邻八村人赶来扑救时,火势早已蔓延开来,哪里还能够扑灭?大火自子时烧至卯时,整座宅子便化为了灰烬,惟剩残垣断壁而已。
自此,义乌县永青岩俞氏,便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2018年5月9日写于淡墨斋
|
评分
-
查看全部评分
|